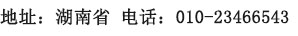白癜风优惠 https://m.39.net/disease/a_5778567.html今天的我们提起日本人,内心往往又爱又恨。对于日本的喜欢,我是如数家珍的。他的动漫自不必说,从承包童年的数码宝贝、火影忍者、多啦a梦,到给我带来无数感动感慨和思考的钢之炼金术师、来自新世界、clannad等神作,这些在国内都有众多漫友喜爱。漫展、动漫周边、Cosplay,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。日本的文学作品也极好,村上春树、东野圭吾等作家在国内的知名度都不错,日本的绯句我也爱读。除此之外,还有电影、日剧、音乐……但想起中日历史,多少又会心怀芥蒂。从九一八开始,十年间,他们在我们国土上杀烧抢掠,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印记,那是不可轻易忘怀的。所以印象中,这是一个擅长创造美,却又不乏嗜血一面的民族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《菊与刀》这本书的作者也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。在书中,她也说到日本人充满矛盾的性情——“温和又好斗、爱美又黩武、尚礼又倨傲、善变又顽固、驯服又专断、忠贞又反叛、勇敢又怯懦…”,既可以专注于如何栽培菊花,但又对武士刀和荣誉充满热情,这也是书名《菊与刀》的含义。那么,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日本人特殊的性情?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呢?作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1等级文化日本特色的儒家纲常日本社会是一个等级极其森严的社会。这样的等级文化体现在两个方面——在政治体系中,他们的行为被政治等级束缚;在家庭中,他们被辈分、性别、长幼束缚。与中国千年来的朝代更替不同,日本人的天皇制号称万世一系。日本古代野史小说《古事记》中记载了第一位日本天皇是神武天皇,传说是日本创世之神天照大神的后裔。自此之后,尽管权力斗争从未停止,甚至武士集团一度架空天皇权力,但从来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情况。反观中国,每当出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时,只要时机成熟,就会有取而代之的现象。无论是三国时的曹魏政权,还是西晋时的司马政权,都是如此。作者将这种等级文化描述为“各居其所,各安其分”——天皇就是天皇,臣子就是臣子,他们就该在自己的位置上,这是绝对不容变换的。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,二战时他们发动战争的一部分理由,也是真诚地希望将这样的等级制度推而广之。发动战争时,天皇在诏书中这样写战争的理由——“万邦各就其位,兆民悉乐其业”。他们认为,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,将西方各国从东亚地区驱逐出去,让各国在国际等级秩序中“各居其所”,而东亚地区则由日本领导建立大东亚共荣圈,帮助落后的东亚兄弟国家。这种等级制度也反映在家庭礼仪之中。女子出嫁之后一切事宜都要听从丈夫的决策,妻子要对丈夫鞠躬,身穿和服时要走在丈夫后面并紧跟丈夫。同辈之中,女孩不论年长还是年幼都要向男孩鞠躬。这种“各得其所,各安其分”的等级制度,可以用《论语》中的话做精准地表达: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但日本人在吸收儒家纲常之时,又做了日本化的处理。中国的儒家纲常之上有“仁”作为最高统领。子曰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,而众星共之。”当帝王有德行,施行仁政,臣子们自然就会“各居其所”。换句话说,各居其所不是儒家的目的,而是“仁”的自然结果。但是一旦帝王不仁,臣子、百姓也是可以不义的。秦王无道,陈胜吴广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。但在日本,“各居其所”成为了目的本身,仁这一概念则被彻底抛弃了,日本人甚至将行仁义贬低为地痞流氓之间杀人越货之类、法律以外的行为。而忠孝则被提升为最高道德准则。那些被中国人嗤之为有些愚忠的行为,在日本眼里则是自然又崇高的。日本人战时的行为便是这种等级制度最好的注脚。在天皇诏书宣战之后,日本人打起战争来可以用疯狂形容,即便已经基本战败,他们依然决不投降,甚至发起自杀式的冲锋。但在天皇宣布停战之后,日本人当天就可以彬彬有礼地迎接外国的记者和士兵。记者们甚至可以轻松地在日本街道上逛街购物。2耻感文化士可杀,不可辱耻感文化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新概念。耻感文化是相对于欧美的罪感文化而言的,它的意思是,人们的善行需要依靠羞耻感来推动,而羞耻的产生需要他人的在场。因为在耻感文化中,不良的行径只要不被人发现,就不会产生羞耻感,也就不必忏悔。这意味着,在耻感文化之中,他人的评价,即荣誉或者说名声,变得极为重要。在本书中,作者就提到了日本画家牧野芳雄自传中关于有关嘲笑的描述。牧野芳雄在家道没落以后曾投靠过一所教会学校,努力学习英语并打算去美国。但当他对一位传教士提及此事时,这名传教士对他的能力表示了怀疑。该传教士对他梦想的嘲弄让他感觉自己的名声收到了玷污,只有实现了自己的目标,他才能洗刷自己的罪名。他在自传中写道:“我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原谅谋杀犯。但是,我绝不原谅嘲笑。”基于耻感文化,牧野认为,必须要成就一番事业以实现对这种嘲笑的报复。最终他的确成功了。这种耻感文化下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,让日本人既强大又危险。曾经日本经济的腾飞一定程度也是由于耻感文化的作用。在耻感文化的作用下,日本极其在意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评价。于是,他时刻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的评价体系之中,并为了得到他国的肯定而不懈努力。于是,明治维新之后,仅仅20年的时间,就完成了西方用了年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。同样的,二战后日本从一片废墟到经济强国也仅仅用了半个世纪。事实上,耻感文化本质上还是依附于等级文化,为维护等级文化服务的。在耻感文化的作用下,由于背离集体行为准则的行为会得到大量的负面评价,因此,这样的行为也就往往不被人们所采纳。这也是为什么,在二战中,即使他们的行为惨无人道,但只要是上级的命令,他们仍然会果断地执行。其实日本的耻感文化同样是受到中国的影响。只是在中国,知耻的标准是道德,而在日本,这样的标准变成了对集体行为准则的完全遵循罢了。3报恩文化人人都是负恩者看日剧时常常有一种感觉,日本人极为客气。一个日本人即使是受到了他人小小的帮助,他也会说,“这可怎么了得,太抱歉了”。对他人赋予的恩情表示极度的抱歉,这就是报恩文化的体现了。恩,一定意义上就是欠他人的人情。日本人认为,“恩”接受后就是一生的债务,报答恩情要积极,要无时无刻偿还这样的恩情。“恩”包括两种,一种是无限数量的恩,也就是所谓的义务,他们包括父母的养育之恩,天皇的恩赐,对自己工作所要尽的义务。另一种恩则是有限的义务,例如对主君应尽的义务,对亲戚应尽的义务,洗刷污名的义务等。事实上,报恩文化同样是服务于等级制度的。在日本,人民爱戴天皇,天皇也会进行回应。人民会因为天皇关心国民而感动地欣喜若狂。“为了让天皇放心”,他们甚至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。通过强调对天皇的报恩,自然而然就加强了等级文化。于是,这种极度强调报恩的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伦理就是,报恩是一种美德,但受恩不是。因为一旦受恩,就意味着欠了人情债,如果不能恰当地“还债”,就会面临名誉受损的风险。这对于日本人来说,是巨大的负担。因此,日本人是极力避免接受恩惠的。比如在日本,大街上发生事故时,人们一般都不太关心,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主动性,而是因为他们认为,任何私人介入都会让接受者背负上他人的恩情。在明治维新以前,日本甚至有一条法律规定:“遇到争端,无关者不得干预”。4理解充满差异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是鲁思·本尼迪克特。她在二战期间受命于美国战时情报局,从她所熟悉的人类文化学的角度,研究日本的民族性。有趣的是,作者从未去过日本,仅通过文献和对在美日本人的访谈,就写出了这本后来被称之为“现代日本学”第一书的《菊与刀》。尽管这本书也遭到一些批评,例如她似乎缺乏历史的视角,将各个时期不同日本人的想法都混为一谈,又比如本书没有考虑到阶级的影响,而仅仅将上层精英的想法作为全日本人的想法加以分析。而由于这本书写于二战,而今天的日本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当我们再去思考日本人性情中的矛盾时,本书的结论也只能作为参考答案,而非标准答案。但本书除了提供给我们人类文化学视角下看待日本人的角度之外,或许更有价值的是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。作者在序言中这样介绍她分析时所秉持的基本前提——人类社会总是在设计自身的生活。如果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被赞同,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将其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,不论困难有多大,他们都将这些结论整合为一体。本书也正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,等级文化、耻感文化、报恩文化,实际上就是日本人为自身所设定的生活方式,他们将等级、羞耻、报恩等一些信念设定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论,并以此展开自己的行动。在今天这个文明与文明,人与人之间不断冲突的世界,最不缺的是标签、是情绪,最难能可贵的是理解。而所谓的冲突,往往不是善与恶对立,而是观念与观念的不同。它们往往没有对错之分,而只是不同而已。意识到这种不同,或者意识到我们是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参考系在观察其他文化,而参考系与参考系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别,这是极为重要的。正如作者在书中说道:人们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事物的。任何民族都将此看做是理所当然,对该民族而言,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焦点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东西。如同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搞清楚镜片度数一样,我们也不能奢望各民族会对自己看世界的方法进行分析。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,眼科医生就被训练出来了,他就会验明度数。毋庸置疑,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承认,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做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眼科医生。我们或许没办法向人类文化学家一样,成为各个民族的眼科医生,但搞清楚自己的镜片度数,去理性地拥抱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,或许没那么难。*吾言*感谢钟吾言公益读书群书友智慧投稿~感觉看完这篇文,我都把《菊与刀》这本书的重点看完了~